文/南方柒玥
灯光、舞美、音乐、演员走位、节奏……细致到每一个动作要配合什么灯光效果,演员表演神态是否到位、动作是否整齐划一。从舞台演员到后台导演,董华兴熟悉所有的舞台,哪怕是演出前的彩排,也容不得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的差错。
董华兴 青年导演、编导 原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舞蹈演员
群舞《顶家女》《倮·印》,文山州文工团两个节目在全国第十二届舞蹈展演舞台中大放异彩,斩获好评。两部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原生态作品,一个柔情似水,一个热情似火,来自文山的舞蹈演员们在“冰”与“火”之间切换,让全国观众赞叹文山少数民族服饰以及舞蹈,认识文山,认识来自文山的傣族和花倮。
从东北沈阳到云南文山,从春晚舞台到文山周庆舞台,从舞台演员到幕后的编导、导演,董华兴越来越清楚自己要什么。关于舞蹈,永远在路上,无关抵达。
“冰”与“火”的舞动
在人群中分辨出这群文山姑娘是不难的,在春城剧院的排练舞台上,和自己较劲,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队形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文山姑娘那股子劲隐藏在她们的身形骨骼和动作曲线中。
说起文山,我们印象里的壮族聚居地。其实,文山州居住着汉、壮、苗、傣等11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服饰让人目不暇接,也由此创作出了多个优秀的舞蹈作品。文山马关县艺术团以当地彝族和彝族支系花倮为背景创作的两支舞蹈讲述他们的民族故事,登上了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的舞台。这也是马关县艺术团的演员们首次站在最高舞台。
《顶家女》
《顶家女》以文山傣族的帽子为创作灵感,其帽子的造型似“人”字形房顶,寓意“顶家走”,被称为把家顶在头上的民族,傣家女儿不管走到哪里,家永远在头上,心永远在故乡。通过肢体语言展现了傣家女儿多姿多彩的生活、热爱家乡、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景,诠释了无论是老者还是纯真孩童,都要传承傣家良好的家风和优秀的传统,体现了家和故乡在傣族女儿心中的重要性。舞到最后,小女孩接过帽子,象征着傣族的传承,把家风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倮·印》
《倮·印》则展现了花倮人作为彝族的一个分支,每逢节日,德高望重的宫头举高脚伞,引领众女性围圈随笙起舞,从头至足踝一刻不停地呈“S”形摆动,动作简洁明快、粗犷热烈,保留了原始舞蹈的神韵,被称为“东方人的迪斯科”。高脚伞是太阳也是方向,更是民族的精神,能为花倮人挡风遮雨,引领着花倮人走向新的幸福生活,在彝族文化发展中烙下了精彩纷呈的辉煌印记。
花倮人服饰以花、黑为主体色调。妇女上身穿较短的无领襟衣,用多种颜色布料裁剪成三角形小块拼合缝制,同时绣有鸟嘴、鸟眼睛、鸟脚等花纹图案。下着裙子为黑色齐脚踝长筒裙,后腰部系上三角形布块和红绒线泡缨制成的飘带,远观似凤凰尾。现在花倮人家基本都为家中女性置备有这套服饰。
两个节目风格截然不同,一个柔情似水,寓意对家园的向往;一个热情火辣,表现对生活的热情。
《顶家女》的小演员
在此之前,《顶家女》曾以舞剧的形式在文山建州60周年晚会上表演过,新颖的表演方式赢得了满堂彩。入选之后,导演董华兴重新进行加工,整个动作加快加复杂。从舞剧改变成舞蹈,以参赛的标准来衡量节目和演员。
“把传统少数民族元素和现代编舞结合,让更多年轻人来关注并且喜欢。”从东北到云南,董华兴希望重新挖掘云南少数民族的舞蹈作品,在原生态的舞蹈动律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创新,希望少数民族的精神能让更多人学习并代代相传……
舞,无关抵达
舞者、编导、导演,85后的董华兴在多个身份之间自由切换。从选手到演员,从舞蹈到舞剧,从竞技舞蹈到幕后编导、导演,舞台上的他阳刚、洒脱、英武,转型编导后,他成为性情温和却在专业素养上极为严厉的老师。
董华兴和演员们在一起
董华兴和云南的缘分很深。追溯到201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云南文山合作编排一个原创民族舞剧《铜鼓姑娘》,那是根据云南省文山州砚山籍王建川烈士的英雄事迹创作的舞剧艺术作品。从此和云南结下缘分,常往云南跑。“云南的少数民族舞蹈相比其他民族有独特性,民族服饰、舞蹈动机都是都很独特。”这几年,他与云南的团队合作出数个作品。
因为这次演出的机缘,董华兴和曾经同台演出的小伙伴在昆明相聚,很多年过去了,老朋友们还在坚持跳舞。1997年的广州、2006年北京的桃李杯,他的记忆里一定还格外清晰。
舞剧《梅兰芳》
查阅网络,关于他的信息太多了。比较密集地集中于他成年之后的作品,《梅兰芳》是很重要的一部。由辽宁歌舞团打造的舞剧《梅兰芳》呈现出大师的艺术人生,舞剧融合了古典舞、民族舞与现代舞。其中《天女散花》一段,董华兴用了一根15米的彩色长绸,挥舞起来似缎似水。机会来源于:2009年,董华兴凭借一段《雪·梅兰》于第八届全国舞蹈比赛夺奖,受辽宁歌舞团之邀编排与梅兰芳相关的剧目,舞剧《梅兰芳》应运而生。梅兰芳之子、京剧名家梅葆玖担任舞剧艺术顾问,霍尊演唱主题歌《花雅禅》。
董华兴与春晚有着不解之缘。2010年,央视春晚节目《追梦》领舞;2017年,央视春晚节目《清风》他是编导。
时间切换到2018年6月,董华兴以导演和编导的身份出现在昆明的舞台上,他带领着一群来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演员走上最高舞台。从舞者到编舞,他说不清到底最热爱哪个身份,如果一定要厘清,对于他而言“舞蹈就是一切,舞蹈就是生命”。
追溯到大约五六岁的年纪,那时就自己琢磨编舞。他说自己是部队培养的,9岁就进了沈阳军区文工团,直到两年前脱下军装。对于部队的感情和感激,他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来说话,他希望能成为全国有名气的导演编导,能排出更多作品献给观众。
“舞蹈无关抵达,因为它永远在抵达的路上。”对于一个舞者的艺术素养,这大概就是终极追求。像是永远在比赛,永不停歇。
传承少数民族舞蹈
这群文山姑娘是第一次登上这样高规格的舞台,激动之余是没日没夜的排练准备演出。
《顶家女》的演员中有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女孩顶起由长辈们传递来的帽子,象征着这台演出落下帷幕。所有的紧张与焦虑不安归零,而下一次演出,又将以同样的状态去面对。
“有点怕他,但很敬佩他,我们发自肺腑喜欢他编的舞。”排练结束后的后台,演员们累到大口喘气。但他们很喜欢这位编导,他编的每个舞蹈都不轻松,但这也是她们最终从容上台并迎来掌声的根基。
韦琦是《顶家女》的领舞,她把文山傣族姑娘表演活了。舞毕,在后台看见她的时候,腿上大片大片的淤青,又青又肿。“这没什么,都习惯了。”她在另一个参演的节目《倮·印》里是群舞的角色。从接到入选通知就再也没有休息过了,两个节目同时排练,同时还在准备9月份云南省青年演员的比赛节目。
她们排练时的专注
同她一样为了舞蹈拼命的,还有二十几位文山姑娘。她们自小习舞,再经过专业舞蹈学校的培养,最后回到家乡文山,继续跳舞,把家乡的少数民族舞蹈传习下去。以舞蹈为语言,让更多人认识了文山。
在一群二十出头的舞蹈队伍里,韦琦显得更加成熟和练达。90后的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今年已经是3岁孩子的母亲了。说到以后会不会让孩子跟她跳舞,“孩子没遗传到我的天赋,”她哈哈一笑,或许有些许遗憾,或许不太想为孩子设定未来。她说,会一直跳舞,她用了好几个“喜欢”来表达。
“你看,小演员的服装就是文山当地少数民族的着装。我们表演时戴的帽子,就是日常佩戴的帽子。”她们舞动着当地少见的、独特的少数民族舞蹈,让全国观众了解文山的另一面。
部分图片来源于《舞蹈中国》
 看看云南
看看云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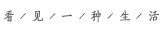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