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放弃城市住进乡村的年轻人,到底图什么?
那个来了很多年轻人的“网红”大墨雨村,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大墨雨村
“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对我们俩来说是这样的。我们更愿意待在大自然里面,那种状态下才是放松的。”
在昆明城郊村子住了一年后,她轻描淡写:没有感觉放弃太多,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即便两人都没有乡村生活的背景,她坦言对于大城市也没有特殊感情,高薪、高水平物质生活都不是他们在意的。
蹭蹭和月明的家
2年前,月明和蹭蹭,一对来自北方的80后“神仙眷侣”:一个程序员,一个生态学硕士,放弃一线城市北京的生活和事业,千里迢迢来到云南,住进一个村子里,自己动手改造农民房。
住进大墨雨村这一年多,他们自己动手改造租来的农民房,建起木工坊。每天,月明去村学给孩子们上课,或进行自然教育;蹭蹭则一头扎进木工坊摆弄木头,偶尔进城给小学生上编程课。心情好的时候,他们一起上山捡木头。
自然爱好者
蹭蹭 不会焊电路的程序员不是好木匠
两个北方人:放弃光鲜亮丽的北京,隐居素不相识的云南
9月,我在距离昆明30分钟车程的大墨雨村见到月明和蹭蹭时,一度感叹“别人的人生”并不总是骗人的。
月明作为“向导”,带领我们一行城里来客游览“网红村”大墨雨村。村口新建起的“洋楼”,与村子深处改造得很艺术的云南乡村土基房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历经300年风雨的彝族村落,完整的保存着土墙、土主庙、各式旧风俗……
大墨雨村闲置的土基房
“嬢嬢,吃饭了嘛”“今天菜都卖完了吗”……沿途村里嬢嬢们打招呼,“在北京的时候,合租在一层楼里,一年不会见几次面,不要奢求有交流。”彻底离开城市的月明,不止一次感慨城市与乡村的差异。
改造后
在他们的家与蹭蹭打照面时,一身风尘仆仆的工作装、长期摸木头和修机器而黢黑的双手……一副典型的“木匠”,令人联想不到,2年前的蹭蹭还是北京写字楼里的程序员。
黑龙江女孩月明,新疆男孩蹭蹭,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相遇相恋直到修成正果。彼时,月明的工作是做自然教育,蹭蹭则是程序员。离开北京的念头是在工作高压中产生的,通勤时间、周末加班,并且“气候啊,生活节奏啊,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与云南的结缘是月明2016年的一次云南旅行,返程后,没多久又带着蹭蹭再访这个自己先动心的地方。3个月后就办好离职手续,把家从北京搬到云南。
蹭蹭和月明
2017年到2018年,亦正是大批北方人来到云南买房置业定居的关键性时间点。但月明和蹭蹭是反向的,在昆明的一家自然教育机构工作一年之后,他们向更偏僻的地方迁徙。2018年3月,彻底告别城市生活,距离昆明市区不远处的大墨雨村,租下一间农民房自己改造,开启彻底的属于他们的乡村生活。
不会盖房子的程序员不是好木匠
上蹭蹭的木工体验课时,他没有教科书式的课程规范。在教会你使用工具之后,全然由你自个去发觉可能性。
他把村里以前的嫁妆柜做成沙发摆在院子里,给家里的猫做了个高科技的喂食机,带着学生们建了间草屋……
嫁妆柜改成沙发
月明说他拥有变废为宝的魔法技能,“木头在他手中不会浪费。”根据树枝形状做成“手”造型摆件;被虫子蛀了虫道的木头做成门牌;有人指定再做一个木头哨子,声线却不一样了……在蹭蹭的工作间,没有长得一样的木头作品。他说能标准化批量生产就没意义了。
木头艺术品丛林中,有件格外醒目:几块圆木拼成人形,弯腰驼背,蹭蹭觉得做着做着特像自己,于是再给它做了个包。
而在月明心里,做木头的最大乐趣,大抵就是“结婚时我们用木头给对方做了戒指。”
彼时窝在北京租来的房子里做木工的蹭蹭,终于在大墨雨村有了整整一个院子的工作室。居住的地方放在二楼,一楼整个露天院子都是工作间,这边堆木材,那边种菜,树上的果子熟透了掉下来,猫捉着玩耍。
租来的土基房,月明和蹭蹭花了好长时间改造。没有推翻重建,请来村里的师傅,在原来的基础上切砖、上梁,加高一层。剩下部分,从装门窗、刷漆,到盖厕所,蹭蹭一点点搞起来。
月明形容他是个结构性思维很强的人,包括木工坊的结构到物件添置,储物空间,也没学过,但就是靠着天分摸索着完成了。收来的二手机器和木材,山上捡来的木头,9.9包邮的红木废料……慢慢堆积成内容丰富的工作室。
蹭蹭的工作间
“我觉得现在生活的就挺自如的,没有哪个时刻觉得特别的艰难。”即便在他们此前的人生里缺失盖房子这项体验。
这大概与他们的生活理念和热爱相关罢了。对房屋没有太高要求,简单的翻修与装饰,反倒与旁边的老房子丝毫没有违和感。没有太多预算,加上15年的房租,大概花了10万,他们拥有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家。
大墨雨村生活的100种可能性
月明和蹭蹭有多重身份,共同融入到一个新老交替的村子中去。
在没有被模板化分割好的每一天中,月明有时一早起来去村学给孩子们上课,夏天带城里来的孩子去山野田间进行自然教育的夏令营,没事的时候就种菜。
蹭蹭呢,有时埋头一整天做定制的木作品,空闲时研究电脑和机器。到了约定的时间进城给小学生上编程课。更多的时候,两人一起上山捡木头,回来给邻居们做做门牌。
“在这儿就不像城里,你只能打一份工有一份的收入,在这边收入是多元的。”他们也不必担忧生活来源。
画家、建筑师、公益人、艺术家、多肉达人……还有做古琴的、玩攀岩的、开民宿和咖啡馆的,办村学、做生态农业的,还有纯粹养老的……“神秘”的新村民!
“我的手机坏了,村群里说一声就有人拿来旧手机‘送给我’。”然后他们给对方做一些木工作为回馈。菜熟了分给其他人,需要借东西群里说一声。基于共同爱好,他们一起攒局:自然农法、自然建筑、中医、占星、舞蹈、女性成长、乐队。
给邻居做的门牌
这种社群的生活理念,延续到与老村民的交流中。月明回忆起至今最盛大的一次活动,是在去年联合老村民一起举办的800人规模团圆饭,还有延续下来每月一次的村集。在日常中,邻居嬢嬢们见面会递给你一把菜,邀请到家里吃饭,他们则帮着修修电视网络什么的。
也因此,大墨雨村和千千万万的农村不一样了。新村民的到来为村里带来了经济收入。但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也担心当地传统文化失传。新村民想办法让这个村庄保持活力,比如开彝绣班,请村里的绣娘教大家做绣花鞋。
“来的人多了,老村民租了房子搬到外面去住,感觉把他们挤走了。”村不再是村,这也是新村民们的担忧的。
另一种生活体验:永续生活
不同于其他“新乡村生活”,100多位新村民,在大墨雨村实践了“永续生活”。
月明和蹭蹭在自家建起生态旱厕,自己堆肥,院子里养鸡种菜,捡垃圾做生态砖。
永续生活的实践是从【丽日】的主理人婷婷开启的,因为认同感大家一道参与起来。
社区仓库
面包房
实际上,做自然教育的月明,在北京生活就在租房的小阳台利用泡沫箱养蚯蚓、堆肥、种菜。来到大墨雨村,有了天然条件,家里干湿分离的生态厕所,不仅节约了用水量,还能堆肥用以种菜。院子里挖了池子,排出的生活污水经植物过滤又变成可再利用的中水。
在大墨雨村没有满天飞的垃圾,他们收集垃圾,进行垃圾分类,做成生态砖用来砌墙。旧衣服旧玩具则收集起来,捐给物资贫乏的贫困山区。
说起永续生活,月明说村里的老人就“很永续生活”,厨余直接喂鸡,地里的枯枝烂叶发酵成肥料,以前洗头用皂角。“他们不需要理念支持,天然就是这么做的。”月明担忧的反倒是年轻人带来不环保习惯。
自己盖房子、做木工、当老师、继续从事自然教育、实践永续生活……在这个“离城又不离尘”的网红村生活一年多后,月明觉得“好像现阶段已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我实现”。
但她又觉得她和蹭蹭的生活方式代表不了大多数。“这种模板可能只存在于跟我们比较类似的一部分人而已。”
大墨雨村会是人生终点吗?
“这里不会是我们生活的终点,15年租期到了我们也才40多岁,到那时,再考虑去其他的地方,寻找人生的下一站。
文/南方柒玥
 看看云南
看看云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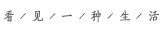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