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8岁的桂焕兰老人还没有退休。
西安马路,除了大观小学不时传来的孩子嬉闹声和稀疏来往的人影,这条夹杂在潘家湾和小西门之间的老街,几乎没什么市井烟火气息。
每天上午,桂焕兰都会缓步走到西安马路,操着一口流利的昆明方言,和街坊寒暄几句之后,走进一家门口挂着白布招牌的老店——“张学成笔庄”。
十几平米的小店,光线昏暗。墙上挂着几面“文明个体户”、“先进个体会员”的奖牌,落款时间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还有几幅字画,来自香港、丽江等地的老顾客。
除此之外,墙面集中挂出了几张裱过相框的报纸,这些采访多为六七年前,标题中所写的“云南老笔匠如今已无传承者”、“百年笔庄面临传承危机”,到现在仍是一个难题。
桂焕兰老人是百年老字号张学成毛笔庄的掌柜,也是昆明最后一位能完成全套制笔工序的人。
张学成毛笔庄,创自清光、宣年间,属南派赣系,与吴兴“湖笔”同一祖源。民国初,为了避兵乱,张家西迁入滇。
最初,张学成毛笔庄生产的毛笔因不合昆明当地的使用习惯,经营惨淡,后来才将原本纤直的笔头改进为云南人喜欢的饱满笔腹。在改革制笔工艺的同时,笔庄又推出发叉保修、当面试写服务,声名减响,先后在正义路、武成路购置路面以“前店后坊”式经营,20世纪30年代在昆颇有名气。
在江西李渡老家,桂张两家同为毛笔世家,不过桂家的名气远不如张学成笔庄的大。上世纪40年代,16岁的桂焕兰从江西远嫁昆明,从此便开始了制笔70余年的生涯。
如果不提桂焕兰的故乡,你很难想象眼前说着昆明方言的老人竟然不是云南人。
“其实我还是带着乡音,你看我说自己的名字,中间的‘焕’读成‘fuan’,那么多年了还是改不过来”,桂焕兰笑称。
从大观街到金马坊,在80年代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都有过张学成笔庄毛笔摊的身影,桂焕兰说,“我们的毛笔摊永远都不缺顾客”。
不过她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修笔头,用刀片一刀一刀梳理笔头上杂乱的毛,剔除废毛,这一道工序能让新制毛笔不开叉。
毛笔挥洒的艺术,是以制笔人的健康为代价的。长期伏案工作很影响视力,桂焕兰现在一只眼睛白内障。十几年前,桂焕兰的丈夫,张学成笔庄的原主人眼睛失明,再也做不了毛笔,变回了老家养病。
“做毛笔患上的疾病很多”,桂焕兰解释道,因为制笔常年与毛发打交道,大量的毛发被吸入体内,容易得呼吸性疾病。
修笔头沾取的粘性液体,是用海浪打在石头上沉积下来的青苔晒干以后制成的,价格昂贵,通常几百块一市斤,把干菜买回来以后,还需经过漫长的熬煮过程才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既不会腐蚀兽毛,还能防止毛笔生虫,所以即便成本高昂但笔庄仍坚持使用这种材料。
在毛笔的108道制作工序中,材料的选择颇为讲究,狼毫要东北冬天黄鼠狼的尾须,羊毫要江浙一带的羊毛,笔杆可以从西山区墨雨龙潭选上好的竹子。
毛笔制作完成以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刻字。桂焕兰近70岁的大儿子专门负责这一项手艺,用锋利的小刀刻下笔的型号和张学成笔庄的标志,再用白粉笔在上面一抹。
“毛笔成品必须满足尖、圆、齐、健,尖就是笔头锐利,圆就是笔头饱满,齐就是毛笔开笔后笔锋整齐,健就是毛笔写起来要有弹力”,桂焕兰说一支好的毛笔不仅要依靠上乘的毛料,还要有好的手艺。
30天,如果按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一个月能生产300-400支毛笔。买上一支毛笔,能用很多年。
过去卖一支毛笔够买2斤肉,如今毛笔大多变成了收藏品,互联网时代的加速发展,使得昆明制笔的老字号慢慢消失。桂焕兰说:“怎么生存啊,如果不是到我这个年纪,生活节奏和水平都供应不上,以前的同行早就改行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百年老字号张学成笔庄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
采访那天快结束的时候,昆明突然下起暴雨,大风刮得树枝摇摇晃晃,雨水打在铁皮屋顶的声音,似乎就是这条平静的西安马路上最热闹的一幕。
桂焕兰老人的儿媳从后院端着接满雨水的盆,把水倒到店铺门前。后院漏雨,遇上这样的天气,抬几十盆水是常事。
接着我们闲聊,“要是真的有一天,奶奶你也不做笔了,估计也闲不住吧”。
“那我来铺里玩玩就走了,还省心。走了走了,我回去煮饭了,还有哪样留恋的。”
“哈哈哈……”这一次,我们的声音终于盖过了门外的暴雨声。
我们都清楚,桂焕兰老人舍不得毛笔,也特别乐意传授制笔工艺,曾经有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向桂焕兰老人拜师学艺,不过最终却都没能坚持下来。
与繁华的小西门临街的西安马路,两边的平房是老的,笔庄的陈设是老的,毛笔工艺是老的,就连时代洪流中最后一位制笔匠人也老了。
“人生有限,穷尽一生陪伴那些即将消失的老手艺,也不过数十年而已。对手艺人来说,再活五百年都不够。”
 看看云南
看看云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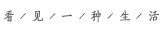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