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昆明,读懂碧桂园” ———昆明城市美好生活系列报道之四
是否可以想象,地处高原且三面环山,本应干旱少雨、缺水干燥的昆明,曾经也是一派水乡泽国的城市风貌。
或许清初“联圣”孙髯翁笔下“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的五百里滇池壮阔景象,现代昆明人已是无福得见,但近代“滇池水一直涌到云南大学门口,并与现今翠湖连为一体”的景象,却曾真实存在过。
不止于此,古桥繁柳、老屋印水,以及36条穿城绕巷的纵横河道和繁忙发达的码头河运,都点缀了老昆明的“水城”形象。难怪冰心在《默庐试笔》中,会用“柔媚的湖水,无际的稻田,青翠的山,斗笠,水牛,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在表现着南国的风光”来形容宛似江南的旧时昆明城。
有人说慵懒、随性、知足是昆明这座城市的性格,熟不知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水说起,不止昆明人在这里乐水而居,就连动荡年代流亡昆明的老舍先生,在看到昆明的“水乡景色”时,也不免感叹“滇池一望无际,湖的气魄,比西湖和颐和园的昆明池都大得多了,在城市附近,有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连诗也懒得作了”。
相关阅读》》
昆明“江湖”往事
70、80时代的昆明年轻一代,他们对于滇池曾经漫过大半昆明城,且清可戏水的憧憬,大多是从父辈,甚至祖辈的口中得来。
每年清明上坟从高海公路经过,父亲总会指着海埂龙王庙附近的水湾,对我们小辈讲述四五十年前他的“滇池轶事”。
“那时滇池就是昆明孩子的天堂,到处都是捉鱼摸虾,或是直接往水里边扎猛子的光屁股男孩,一整个暑假无聊的时光都可以在这里打发,有时甚至为了占一个摸鱼捉虾的好位置,天不亮就用饭盒装好隔夜冷饭和咸菜,约上小伙伴徒步到滇池‘洗澡’。”
虽然我不太能理解父亲那个年代的“滇池乐趣”,但从他的叙述中能够想象,那时候的滇池水不光清澈,更滋养了独有的昆明生活方式。只是在70年代末的一个饥饿冬天后,昔日绿荫覆盖的滇池湖岸和晶莹剔透的湖水,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片黄褐色的土石滩。
1970年,在飘舞的红旗布标和隆隆作响的炸石炮声映衬下,让昆明全城居民都处于亢奋,而“向滇池要田、向滇池要粮”的“围湖造田”运动,不光夺走了父亲那代人的欢乐,同时也拉开了昆明和水的距离。
滇池的“围湖”运动开始时,8岁的父亲因为学校停课只得每天跟着爷爷在滇池边上工。父亲清楚的记得,一车车土石倾入滇池后,原本清澈的滇池水翻起一滩泥流,而当一片围堰区完成填埋后,水面会变成泥潭,泥水里还会看见已经死去,或张着嘴挣扎将死的鱼。
那一整个夏天,父亲都泡在滇池里,但却没有了原来的快乐,用父亲的话说,不光是因为滇池的水变浑了,还由于类似“十万军民向滇池进军”的亢奋标语和开山炸石回荡全城的隆隆炮声,让日子不再轻松无虑。
从那以后,直到“围湖造田”运动结束,父亲再没去过滇池边,他给爷爷的理由是看一群人往滇池倒土没意思,实际上却是心疼那些在泥潭中无法呼吸的小鱼小虾,和滇池湖岸变成支离破碎的滩涂。
为了保证“围湖”的质量,许多流向滇池的小河都被切断堵死,滇池成了溢满污血的“心脏”,而城内原本的生机盎然,也因为一条条死气沉沉的水道而变得阴郁。
小孩近水会挨训
当然,除了围湖造田的阴霾,父亲关于滇池的记忆,更多的还是与美好有关,亦如那个年代年轻人羞于说破的青涩回忆。
“那时候男女同学约会,大多数会选择到滇池边,一来有山有水的环境比较浪漫,二也是为了躲避家长和街坊的目光。而为了能够与女同学二次交流,‘泳技’自然就成了男同学间一争高下的‘必选动作’。”父亲满脸幸福地回忆。
“为了获得女同学的青睐,每次我都会把游回来的力气也一口气使完,游到划定安全范围的浮标外,可是等爬上岸才发现,每个女同学都有了聊天的对象,有时候甚至还会因为累脱了力,耽误回家吃晚饭的时间。”父亲略带骄傲的说。可每当我们听他“吹嘘”泳技但又无缘与女同学单独相处的时候,总会“抬杠”似得玩笑道,“肯定是你技不如人,要么就是压根儿就没人看得上你……”
到我们这代,虽没有父亲口中那般的滇池“见识”,但“玩水”也伴随了我们的整个童年。
“捉蜻蜓”绝对是每一个80后昆明男孩童年必备技能之一,除了常见的网捕外,当抓到大个儿的绿蜻蜓时,就会用奶奶缝被子线拴住蜻蜓身子,让它在空中飞舞,吸引飞来交配的蜻蜓再轻松抓住。而这种捉蜻蜓的方法,一般在靠近水的地方比较奏效,那时的翠湖,自然就成了男孩们捉蜻蜓的圣地。
每个夏天,街坊的男孩都会聚到翠湖边追赶蜻蜓,只是看到翠湖边钓鱼人正襟危坐等待小鱼上钩的高深模样后,一些男孩回到家就会把自己捉蜻蜓的网兜改造成钓竿,第二天扛着鱼竿到翠湖边学起了钓鱼。
相比钓鱼,好动的我还是更喜欢追赶蜻蜓的疯跑,不过看到其他小伙伴满载而归喝鱼汤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些眼红。
于是,每天早上拿着购买一套烧饵块的5角钱,在菜市口单买一个不夹油条的饵块,省下来的2角钱则用来买两根鸡肠子,然后用吃完的饵块袋子包好,等捉蜻蜓跑累了,就会找个离翠湖水面近的树荫,用手提着鸡肠子放到水中,一两分钟就会顺着鸡肠子夹满大大小小的小龙虾,有时候运气好还会收获个头不大的螃蟹。
等两根鸡肠子都被虾钳夹的不成样子,钓上来小龙虾也够一顿饱餐,便用捉蜻蜓的网兜装了虾蟹扛在肩上往家走,本想到家后虾蟹加餐可以收到父母的几句表扬,怎想换来的却是一顿“细竹炒肉”和三天不准出门的警告。或许是可怜我挨打受骂,一盆的虾蟹还是为当天的晚饭加了菜。
后来才知道,父母生气是担心孩子跌入水中发生危险,直到现在,小孩要是擅自跑到水边,家长也会一把拽回孩子佯怒着在屁股轻拍几下,并厉声交代不准离水太近。
虽然挨了打,但“鸡肠钓虾”并未停止,小伙伴们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约定,无论钓到多少虾蟹,我们就自己生火囫囵烤熟解决掉。而对于一些年纪稍长的男孩似乎不屑翠湖的“狭窄”,他们的“钓场”一般都设在盘龙江边,不止是因为江岸里盘龙江水面太远,还因为那里可以捡到螺蛳。
我们还在唱歌跳舞
有人说,“昆明人爱水,是因为昆明这座内陆城市没有太多看水的机会”,但实际上,生长在滇池边的昆明,自古便是一座水城,不止城中仍保留了许多与“湾”、“桥”、“塘”相关的地名,一座内陆城市几乎人人会游泳,也更说明了昆明的“水城”特征。
记得小学的一个暑假,家长开始流行为孩子报各种兴趣班,而我则被强迫送去学游泳,面对我因为暑假不能为所欲为的生气抱怨,父亲的理由是,昆明是座水城,城里河流交错,如果上游的松华坝垮了,大水会淹过整个昆明城,只有会游泳的人才能游到房顶上不被淹死。
我害怕被淹死,于是下决心学游泳,而为了上下班接送方便,那时我学游泳的地方就在老工人文化宫附近。每次学完游泳坐在父亲单车后座回家路过盘龙江时,他总会笑着问我学会游泳想不想到盘龙江里游一圈,但看着那时已经开始变黑的江水,我都会用一副厌恶的嘴脸大声拒绝着。
到了中学,一次从大观楼坐船直接进入滇池的春游经历,多少让我感受都了父亲口中滇池的壮阔。从大观楼的楼外楼码头一路向西驶离城区,沿大观河进入草海,水面逐渐开阔,想起小时候连翠湖一潭池水也担心失足掉落就爬不上来的幼稚想法不禁好笑,而当船开入滇池,看着望不到边际的水面和远处如画屏的西山,更加相信父亲说“发大水昆明全城将被淹没”并非危言耸听。
而那次游船经历,除了感叹滇池的壮阔外,记忆最深的就是滇池沿岸的严重污染。出大观码头,大观河两岸的水葫芦几乎将河道完全阻断,一路灌鼻的水腥味和墨绿色的湖水,让本该爱水的昆明人提不起半点喜爱。直到滇池大坝码头附近,水葫芦的生长才逐渐稀疏,但以往能够看到鱼虾觅食的清澈水体已不复存在。
当年的“围湖造田”和近年开发建设及城市排污的影响,让“水城”的历史始终与昆明的繁华保持着距离,而老一辈昆明人爱水、亲水的生活作风,也为城市化进程的势不可挡所左右。
随着年纪的增长,虽然我知道昆明被水漫过的地方,不再只有滇池、翠湖、盘龙江、大观楼,但对于大多数昆明江河湾涂的认识,都只局限于书架上和网页中的无数文字资料,偶见一段艰难爬过林立高楼露头喘息之后,又被没入丛生大厦的河道,也不能准确唤出它的名字。
所幸,老昆明传承的“水城”性格并未改变,叫做“海边”的滇池畔依旧还有很多昆明人在茶余饭后到那走走,而盘龙江两岸唱歌跳舞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看看云南
看看云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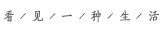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